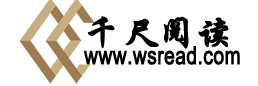青梧寄云岫(沈知意谢云岫青梧)全文免费_(沈知意谢云岫青梧)青梧寄云岫后续阅读(沈知意谢云岫青梧)
《青梧寄云岫优秀文集》 小说介绍
主角叫沈知意谢云岫青梧的是《青梧寄云岫》,本的作者是沈知意最新写的,书中人物感情描写生动形象,主要讲述了: 沈知意捡到谢云岫时,是暮春。破庙的蛛网蒙着灰,檐角垂落的冰棱刚化尽,滴在青石板上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他缩在神龛下,怀里死死搂着半块发霉的麦饼,小脸烧得通红,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。那年她二十岁,刚从父亲灵前
《青梧寄云岫优秀文集》 第1章 免费试读
沈知意捡到谢云岫时,是暮春。破庙的蛛网蒙着灰,檐角垂落的冰棱刚化尽,滴在青石板上,
溅起细碎的水花。他缩在神龛下,怀里死死搂着半块发霉的麦饼,小脸烧得通红,
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。那年她二十岁,刚从父亲灵前接过沈记布庄的账本,
素色裙裾沾着赶路的风尘,蹲下身时,他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,猛地张口咬在她手腕上。
齿尖刺破皮肉的疼漫上来,沈知意却没动。她看着他眼底的惊惶,
像看到了三年前父亲骤逝时的自己——天塌了,却连哭的资格都没有。她慢慢摊开另一只手,
掌心是颗用油纸包着的蜜饯,是她刚从布庄柜上拿的,本想路上解馋。“别怕,
”她声音放得很柔,像哄院里那只刚下崽的母猫,“我不是坏人。”他大约是饿极了,
也或许是蜜饯的甜香钻了空子,松口时,嘴角还沾着她的血。沈知意解开披风裹住他,
那披风是母亲留的,青梧枝的绣样被岁月磨得发浅,却还带着淡淡的艾草香。
他在她怀里抖得像片落叶,却攥紧了她的衣襟,仿佛那是浮世里唯一的锚。带回沈府那天,
管家看着她腕上的牙印直皱眉:“大小姐,这来历不明的孩子……”“留下吧。
”沈知意摸着他滚烫的额头,他烧得迷迷糊糊,却在她碰到他时,往她怀里蹭了蹭,
“就叫云岫,谢云岫。”她想起父亲教过的句子:“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。
”盼他往后能活得自在,不像自己,被这沈府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。谢云岫病了半月。
沈知意在他榻前守了半月,夜里就趴在床边睡,布庄的账目堆在案上,积了薄薄一层灰。
他退烧那天,她正对着算盘核账,忽然感觉衣角被轻轻拽了拽。低头看时,
他睁着乌溜溜的眼,小声叫:“阿姐。”那声“阿姐”,像颗石子投进沈知意沉寂的心湖。
她教他读书,他就搬个小凳坐在她书房,看她握着狼毫批注账本,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发顶,
绒毛都泛着金;她教他打算盘,他笨手笨脚总打错,被她敲了手心就红着眼眶,
却还是攥着算珠不肯放;她去布庄理事,他就蹲在柜台后,看她对着难缠的客商从容应对,
有人想占她便宜,他就梗着脖子冲上去:“不许欺负我阿姐!”他像株藤蔓,
悄无声息地缠上了她这棵青梧。沈记布庄的老主顾都知道,沈大小姐身后总跟着个小尾巴。
那孩子眉眼清俊,就是不爱说话,唯独看沈知意的眼神,黏得像糖。有次她去城郊收棉线,
遇着暴雨,回来时浑身湿透,刚进门就打了个喷嚏。夜里她伏案对账,
忽然听见轻轻的敲门声,谢云岫端着碗姜汤站在门口,小手烫得通红:“阿姐,喝了不生病。
”姜汤熬得太辣,她喝得眼圈发红,他却紧张地问:“是不是不好喝?
我再去煮……”“好喝。”她拉住他的手,他的掌心有层薄茧,
是帮布庄的伙计搬布匹磨出来的,“云岫长大了。”他那时才十岁,却把这句话记了许多年。
谢云岫十二岁那年,沈府遭了贼。夜半时分,她被响动惊醒,刚推开房门就见个黑影窜出来,
手里还拎着她母亲留下的首饰盒。她想也没想就追上去,却被那贼推倒在地,
额头磕在石阶上,顿时血流如注。“阿姐!”谢云岫不知从哪里冲出来,手里举着个砚台,
狠狠砸在那贼后脑勺上。那贼闷哼一声倒了,他却扑到她身边,手抖得不成样子,
想碰她额头的伤,又怕弄疼她,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:“阿姐,你疼不疼?
我去找大夫……”“没事。”她按住他要跑的身子,他的手冰凉,却攥得她很紧,
“云岫保护了阿姐,是不是?”他哭着点头,眼泪滴在她流血的额头,温热的。那天夜里,
她躺在床上,他就坐在床边,替她扇扇子驱蚊,直到天快亮才趴在床边睡着,
睫毛上还挂着泪。沈知意看着他沉睡的脸,忽然觉得,这沈府好像不再那么冷清了。
日子像布庄织出的锦缎,一天天铺展开。谢云岫长到十五岁,已经比沈知意高了半个头,
喉结微微凸起,说话时带着变声期的沙哑。他开始帮她打理布庄的事,账算得比老掌柜还精,
跟客商周旋时,眉宇间竟有了几分沉稳。只是在她面前,他还是那个会脸红的少年。
她替他整理衣襟,他会耳根发烫;她夸他布庄的账目做得好,
他能偷偷乐上半天;有回她绣帕掉在地上,他捡起来时不小心碰到她的手,
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回,空气里飘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。沈知意最先察觉不对,
是在他及冠那天。按规矩该给他置备新衣裳,她挑了块宝蓝色的锦缎,夜里在灯下缝制,
忽然听见窗外有动静。推开窗看时,谢云岫站在海棠树下,月光洒在他身上,他望着她的窗,
眼神亮得惊人,像藏着整片星空。四目相对的瞬间,他慌忙低下头,耳尖红得要滴血。
沈知意关了窗,心跳得像擂鼓,手里的针一下扎在指尖,血珠落在锦缎上,像朵突兀的红梅。
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他。他送来的茶,她让丫鬟接;他想跟她去布庄,
她找借口推脱;夜里他来书房问功课,她总说“太晚了,明日吧”。
谢云岫像被霜打了的茄子,蔫了好几天。直到有天布庄的伙计来报,说城南的张老板赖账,
还动手打人。沈知意正想亲自去,他却站出来:“阿姐,我去。”他去了整整一天,
回来时嘴角带着伤,却把银子一分不少地拿了回来。“张老板说,往后沈记的布,他全要了。
”他笑得有些得意,像只讨赏的小狗。沈知意看着他嘴角的淤青,心里又气又疼,
抓过他的手就要看:“有没有伤到别处?”他却反手握住她的手,
她的指尖还带着绣活的薄茧,在他掌心轻轻颤。他的手心滚烫,烫得她想抽回,
却被他攥得更紧。“阿姐,”他声音很低,带着压抑多年的情愫,“我不是孩子了。
”沈知意猛地抽回手,后退半步,撞在桌角上,疼得倒抽口冷气。“云岫,你是我养大的,
我是你阿姐。”她别过脸,不敢看他的眼睛,“这话不许再说。”那天之后,
谢云岫像变了个人。他不再黏着她,只是默默做事,布庄的账目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,
连最难缠的客商都对他赞不绝口。他看她的眼神,却多了些她看不懂的东西,像深潭,
藏着汹涌的浪。他十八岁那年,考中了秀才。沈知意替他收拾行囊,想送他去京城赶考,
他却迟迟不肯动身。“阿姐,我不走。”他站在她面前,身形已经挺拔如松,
“我要留下来帮你。”“傻话。”沈知意把一方砚台塞进他包袱,那是他十岁时她送他的,
“你该有自己的前程,不能困在这沈府。”他忽然抱住她,下巴抵在她发顶,
声音闷闷的:“阿姐,我只想守着你。”沈知意浑身一僵,推开他时,眼眶红了:“谢云岫,
你再这样,我就……”“我知道了。”他打断她,往后退了一步,深深看了她一眼,
那眼神里的痛,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,“我去京城。阿姐等我回来。”他走那天,
沈知意没去送。她站在布庄的柜台后,听着街上的马蹄声渐远,手里攥着块他常穿的青布,
布料上仿佛还留着他的体温。谢云岫在京城一待就是七年。起初他每月都寄信回来,
说国子监的趣事,说京城的雪下得比江南大,说他得了先生的赏识。后来信越来越少,
偶尔寄回些东西:南边的荔枝用冰窖镇着,送到沈府时还带着寒气;西域的宝石打磨成簪子,
流光溢彩;江南的云锦裁成裙料,比沈记最好的料子还要软。
沈知意把这些东西都收在樟木箱里,却从不穿不用。她依旧守着沈记布庄,
只是鬓角悄悄添了几缕白发,眼角的细纹也深了些。有次布庄的老掌柜看她对着账本发呆,
忍不住说:“大小姐,谢公子如今在朝中做了大官,您该……”“他是他,我是我。
”她合上账本,声音有些发涩,“他年轻有为,该娶个体面人家的姑娘。”话虽如此,
夜里她却总做噩梦,梦见他在京城遭人欺负,梦见他生病没人照顾,惊醒时枕巾总是湿的。
谢云岫二十五岁那年,成了朝中新贵,官至吏部侍郎。消息传来那天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