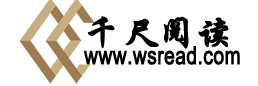像晴天似雨天(戴安克劳斯)全文免费_(戴安克劳斯)像晴天似雨天后续阅读(戴安克劳斯)
《像晴天似雨天精选小说》 小说介绍
主人公是戴安克劳斯,书名叫《像晴天似雨天》,是质量非常高的一部文章,超爽情节主要讲述的是: 声明:本篇小说立意是反对战争。11940年,英格兰肯特郡上空。座舱里的烟雾越积越重,呛得克劳斯睁不开眼。他能感觉到右侧机翼在燃烧,火苗顺着撕裂的金属往回倒卷,空气里都是油和焦糊的味道。引擎偶尔发出一声带
《像晴天似雨天精选小说》 第1章 免费试读
声明:本篇小说立意是反对战争。11940年,英格兰肯特郡上空。
座舱里的烟雾越积越重,呛得克劳斯睁不开眼。他能感觉到右侧机翼在燃烧,
火苗顺着撕裂的金属往回倒卷,空气里都是油和焦糊的味道。
引擎偶尔发出一声带着金属杂音的哀鸣,整个机身在风压里发抖,仿佛一头被困住的野兽。
他的手还紧紧握着操纵杆,指节发麻,手套被汗水湿透,贴在掌心里越来越不舒服。
他咬着牙,尝试拉起机头、调整方向舵,可飞机毫无反应。克劳斯松开了手。
风带着冷意灌进舱口,带走了引擎残存的温度。他仰靠在座椅上,闭了闭眼。那一刻,
脑子里浮现的不是命令、不是地图,也不是机场的喧嚣,而是父亲在书房里填烟斗的手,
窗外一盆盛开的天竺葵。阳光透进来,照在红叶上,很暖,很安静。
引擎最后的轰鸣像是在远处。机头缓缓下沉,地面在视野里快速放大。肯特郡起伏的丘陵,
矮树和青草全都扑面而来。他没有挣扎,也没有拔伞,只觉得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往下拽,
筋疲力尽。泥土和草叶的气味混杂着引擎的焦糊,在最后一刻撞进他的呼吸里。一声闷响,
他想他干脆就这样死在这里好了,对他来说噩梦就能结束。……戴安喜欢肯特郡的雨。
那不是瓢泼的大雨,而是阴沉天空下细密、没完没了的雾雨,
把远处的丘陵和树林都染成了淡淡的灰色水彩。空气潮湿又带着青草的清新味,
让人暂时忘记了战争的硝烟——、哪怕只是短短片刻。南京的冬天,
也是这样潮湿冰冷的空气。戴安有时会在夜里醒来,窗外细雨绵绵,泥土和青草的气味,
和家乡的冬天别无二致。只是,她早已离开了南京。战争像一场无声的瘟疫,
将她从熟悉的土地连根拔起,漂泊到了遥远的岛屿。
她原以为自己会一直留在南京……在伦敦医学院完成学业后,
带着最先进的外科理念回到故土的医院。但现在,那座医院已经在战火中化为焦土。
所有的归程都被堵死,她只能再次踏上流亡的路。回到英国后,
她避开伦敦的喧嚣和压抑的防空洞,选择留在这片僻静的肯特郡乡村,
成了村里唯一的全科医生。这里的寂静是一种微妙的慰藉,让她可以在无声的生活里,
假装战争并未波及到自己。她每天的生活被细碎的事务填满:早上六点起床,
给院子里那株枯萎的玫瑰剪枝,喝一杯淡咖啡,然后步行去诊所。
农夫带着被锄头划破的手掌来找她,孩子发烧咳嗽,老人们要她帮忙配新的关节膏药。
她总是耐心、冷静,语速不急不缓,动作熟练而温和。
村民们尊敬她——“那个中国来的好医生”却总在称呼和距离之间,
悄悄地加上一道礼貌的分界线。她的英语很标准,带着点学院派的冷清,不容易让人靠近。
午后,诊所安静下来,她会靠在窗边的藤椅上,望着窗外的田野和低矮的灰色天幕。偶尔,
她会想起南京的街道,母亲低头绣花的样子,还有医院走廊里熟悉的铃声。但更多的时候,
她让自己忙起来。每一刻都被病例、处方、换药和嘱咐填得满满当当,
不留一点空隙给回忆渗透进来。只有在很偶尔的夜晚,她才会卸下白天的盔甲,
独自坐在狭小的厨房里,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,发呆很久。风雨声敲打着窗棂,
像是从遥远的南京传来的回声。天刚蒙蒙亮,肯特郡的雨依旧没停。
戴安穿着厚重的羊毛外套,挎着藤篮踩进泥泞的田埂。雨水顺着她额前的黑发滴落,
落在手背上,已经分不清是汗还是雨。她低头辨认一丛毛地黄,
脑海里自动浮现出它的拉丁学名和药理用途。只是刚蹲下身,还没采摘,
空气里突然飘来一股不属于这片清晨的味道。是油烟味,很重,像谁在灼烧废铁。
她抬头望去,只见远处树林的另一头,升起一道笔直的黑烟,突兀地***灰蒙蒙的天色里。
2戴安愣了一秒,本能地攥紧了篮子的提手。她不是没有见过事故,但每一次突发,
总能让她心里紧上一根弦。她快步穿过潮湿的草丛,灌木刮在裤腿上,泥水溅到靴子里。
那道烟越来越近,空气也变得呛鼻。穿过一片滴水的蕨叶,金属和焦油味扑面而来。
飞机残骸横在田野里,扭曲的铁皮像开膛的野兽,火星还在冒着烟。地面泥泞,
被汽油和血染成难以辨认的颜色。她一眼看见那个人——飞行服已经破碎不堪,
一条腿诡异地歪向一边,鲜血和泥水混成一滩。他的脸被划伤,金发打结,嘴唇干裂,
呼吸细弱,却还在呻吟。戴安停住了脚步,手指微微发颤。她强迫自己屏住呼吸,
只花了一秒就做出了选择——藤篮被随手丢进一旁的野草里。她跪进了湿泥中,
手已经伸向那人的脉搏,语气镇定地低声自语:“没事,先止血。
”雨水拍在她的后颈和肩膀上,她已经无暇顾及,只剩下医者的本能的责任。
她的指尖沾满了雨水和血,动作一贯的冷静而专业。解开扣子,检查气道,
摸到颈动脉那细弱的跳动,又掀起那条被鲜血和泥泞遮住的小腿,看见金属碎片嵌进肉里。
她深吸一口气,从医疗包里取出止血钳和绷带,动作快速而利落。男子在剧痛中微微抽搐,
喉咙里发出一声混杂了恐惧和求生本能的低吟。戴安抬手,想要用酒精棉擦掉他脸上的血污。
可是,当棉球掠过他破损的衣领时,她的动作突然停住。徽章——一只鹰,
爪下紧紧攥着万字符。油污已经糊住了一半,可那轮廓再熟悉不过。戴安的心跳,
忽然在这一刻变得很重。德国空军。一瞬间,她的脑子像被什么利器划开。
战争的阴影卷土重来。她闻见火药、泥土和烧焦机油混杂的气味,
像回到了南京沦陷的那一天。脑海深处,有什么在尖叫。不是她自己的声音。
那是南京城的呐喊——那些被刺刀穿透、鲜血四溅时爆发出来的、她再也无法忘记的声音。
火光,浓烟,倒塌的牌坊。同样笔挺的军服,麻木的面孔。鲜血沿着青石板路流淌,
汇成一条见不到头的小溪。她曾跪在这样的血泊里,徒劳地摇晃着一个再也不会睁眼的人。
愤怒和悲伤,像烈火一样烧灼着她的眼睛。这个德国人,和那些日本士兵,有什么区别吗?
他们都是战争的制造者,双手都沾满了无辜者的血。她攥着手术剪的手,
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。一边是救命的本能,一边是报仇的冲动。
仿佛有两股力量在身体里撕扯。手里的剪刀悬停在空气中,寒光几乎贴上了男人的喉结。
她看着他苍白又满是污血的脸,耳边只剩下雨滴敲打帽檐的声音。“只要轻轻一下。
”她的理智冷冷地提醒,“他就永远不会醒来。”地上的男人又呻吟了一声,很轻。
却敲打在戴安的心房上。她颤抖的手停住了,她看到了他的伤口。弹片狰狞地嵌在肌肉里,
血肉模糊,再不处理,感染会要了他的命。败血症。截肢。死亡。教科书里的词汇,
冷静地在她脑中排列。伦敦大学那位白发苍苍的教授,
用浑厚的苏格兰口音说:“你们面对的,永远先是一个病人,其次才是他的身份、他的罪孽,
或是他的美德。”戴安闭上眼睛,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里有雨水、青草和血的味道。
再睁开眼时,她眼中仇恨的火焰熄灭了,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烬。她不是法官。
她也不是刽子手。她是一名医生。她松开了紧握剪刀的手,将它轻轻放在一旁的医疗包上。
“你可以死,但不能死在我手里。”她低声,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。她继续包扎,
手却冰得发麻。3处理好伤口后,戴安站在那片潮湿的树林间,犹豫片刻,还是做出了决定。
她四下张望,确认四周无人,这才咬紧牙关,
俯身把那个德国飞行员拖到附近一间废弃的小窝棚里。
那是村里人早年间用来存放农具的地方,如今早已荒废,几乎没人会来。一路上,
她几乎是拖拽着他的身体,湿滑的泥土沾满了她的鞋和裙摆。每前进一步,
她都在心里反复权衡着这样做到底对不对?可她最终还是停不下来。窝棚的木门半开着,
里面阴暗潮湿,只有角落里残留着些干草。她费力地将克劳斯安置在干草堆上,
又脱下身上厚实的羊毛外套,轻轻盖在他身上。她的手冻得有些僵硬,
却还是用树枝和绷带为他做了一个简易夹板,细心地固定好那条断腿。
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医疗专业的习惯性克制,但她的呼吸却因紧张和用力变得急促。
收拾妥当后,戴安抬头看着这张苍白的脸,心头百感交集。她知道自己不能把他带回村子,
否则,一旦身份暴露,他绝无活路。她在心里默默盘算:还需要干净的水,需要药品,
需要食物。她低头再次检查了一遍他的包扎,然后才推开破旧的木门,冒着雨风,
快步消失在密林之间。临走时,她回头望了一眼那间窝棚。雨幕把一切都包裹起来,
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从未发生过。第二日,窝棚的木墙缝隙里透进一缕清晨的光,
斜斜地照在克劳斯的脸上。他费力地睁开眼,瞳孔一时无法适应明暗,
四周的景物都是晃动又模糊的。头痛,腿更痛。意识依旧断断续续——有引擎的嚎叫,
有潮湿泥土的气息,有绿色的田野和残破的记忆碎片。这时,
他看到角落里蹲着一个东方女人。她披着深色的毛衣,正在用酒精炉煮什么东西,
水雾在晨光中升腾,把她的侧脸勾勒的很好看。他动了动,喉咙干涸,发出一声极低的哼声。
女人警觉地回头,黑发微微散乱,眼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疏离感。
“Wo bin ich?” 克劳斯的声音很哑。(我在哪里?)她显然没听懂,
眉头拢起了一道防备的褶皱。犹豫片刻,她端起小锅,把煮好的麦片粥倒进碗里,
缓缓走近床边。她举起勺子,示意他张嘴。克劳斯没有动。他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把握,
也说不清这个女人是敌是友。可胃里那股让人失去理智的饥饿感最终胜过了警惕。
她的手很稳,动作克制,有着医生独有的耐心和距离感。粥很烫,却也温热。
他吞咽下第一口时,暖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,一点点化开他身体的麻木和寒意。那一刻,
他才终于确认,自己还活着。窝棚外,雨后的田野安静得几乎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。两个人,
一个喂食,一个咽下,彼此沉默着,都在异国清晨,短暂地对峙着。
戴安总会挑在天色未亮、或林子被暮色淹没时来窝棚。她告诉村里人,
说在林中发现了一些珍稀药草,需要定时照看。理由简单,却没人怀疑。每次来,
她都带着一点食物,干净的绷带,或是自制的草药膏。草药气味苦涩,克劳斯皱过眉,
但从未拒绝过。偶尔,她会帮他检查伤口,
用平静的语气低声提醒:“Don’t move.” 他能听懂片段的英语,
就像她能记住几句简单的德语。两个人之间的交流,慢慢变得不再只是沉默。有时,
她指着水壶,说:“Water。”他点头,轻声重复:“Wasser。
”他指着林子外的云天,慢慢念:“Himmel。”她笑了下,柔声回答:“Sky。
”他们的语言总是磕磕绊绊,但彼此都有足够的耐心。语言的墙很高,
却在两个人真诚又笨拙的交流下,被一点点凿开缝隙。夜深时,他发起高烧。意识模糊中,
他在用德语低声呓语,时而喊着“Mutter”(妈妈),时而念着谁的名字。
戴安整夜守着他,温水一遍遍擦拭他的额头,药膏重新涂抹,窗外雨点滴滴答答。
她看着他痛苦的表情,只觉得那是个需要被救治的人。等烧渐渐退去,克劳斯清醒了不少。
他挣扎着想表达什么,从地上捡起一根烧黑的树枝,在泥地上画下一架飞机,
又在旁边画出爆炸和火焰,最后画上一个深深的“×”。他抬头看她,眼神很沉。
那里面没有胜利者的骄傲,只有一种让人疲惫的厌倦和拒绝。戴安明白了,
她沉默着接过木炭,在地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十字。然后,指了指自己,
低声说:“Doctor.”克劳斯看着她,终于点了点头。
那些原本说不出口的歉意、无力和理解,就在泥地的图案和简短的词句里,悄悄蔓延。
4克劳斯总是喜欢安静地看着戴安处理伤口。她动作很稳,草药膏涂抹时,
伤口疼得他浑身冒汗,却不知为何,每当她靠近,胸腔里那种彻骨的孤独似乎会淡下去一点。
她开始用更细致的方式教他英语。每次来,总会带一本磨损得厉害的儿童英文读物。
她坐在地板上,指着插画,缓慢地发音:“House。”克劳斯迟疑着学:“Haus。
”“Tree。”“Baum。”“Bird。”“Vogel。
”他们在窝棚昏暗的光线里,断断续续地交换着词语。语言绊住了彼此,
却也变成一根可以慢慢攀爬的细绳。每一个音节,都像是小心翼翼的探路石,
让他们一点点找到对方的位置。一天傍晚,戴安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,
从藤篮底下摸出一个苹果。苹果并不漂亮,皮上还有疤痕。她什么都没说,
只是把它放在克劳斯旁边,转身消失在暮色里。窝棚渐渐暗下来。外面风吹过树梢,
带着远处田野的泥土气息。克劳斯没有立刻吃那个苹果。他把它拿在手里,
手指不自觉地来回摩挲着那层粗糙的果皮,感受着这个东方女人的给与的温暖。
他目送她离去的方向,在这座陌生寒冷的岛上,第一次,有了些微弱却真实的温度。
克劳斯有时候会想,如果能就这样一直躲下去,是不是也未尝不可。不用再听见轰鸣的引擎,
也不用再看到硝烟和血。世界很小,只有雨声、草药气息,
还有戴安每次带进窝棚的淡淡温度。可秘密,总有被阳光照亮的那天。发现它的,
是村里邮差的小儿子汤米。那天下午,他不想上算术课,独自钻进林子。刚拐过那片矮灌木,
他发现一块被反复踩实的湿地,和一截血迹斑斑的纱布,丢在半掩的树根下。
那不是猎人会留下的痕迹。小男孩盯了很久,把这事儿告诉了他哥哥。
他哥哥又当作新鲜事和大人讲,酒吧里杯子还没擦干净,这个流言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庄。
“戴安医生在林子里,藏着什么。”第二天早上,戴安走进村口,气氛就不对了。
村子安静得出奇。平时会热情打招呼的几个人,今天都不约而同地低下头,
眼神里藏着陌生的警觉和探问。她的步子没有停,但手心开始冒汗。每走一步,
脚下的泥地都踩得比平时重。她知道,这一天迟早会来,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
她照例绕进林子,走到窝棚前。几只喜鹊在树上蹦来蹦去,林子里静得只有风声。
给克劳斯换完药后,正当她收拾药箱准备离开时,外头忽然传来一阵人声,
先是几个人的脚步,很快变成了一片低语和粗重的喘息。她脸色倏然苍白。窝棚门外,
不只一双眼睛在等待。克劳斯也察觉到了不对劲,费力地撑起身体,目光里全是警惕和紧张。
戴安冲他做了个安静的手势,深吸一口气,把背挺得笔直。她知道,她必须自己走出去。
她握紧门把,推开窝棚的门。潮湿的空气中,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。
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安和怒意。5阳光照在林间的空地上,十几个人围成半圈。
村长、酒吧老板罗伯特、铁匠,还有那些戴安曾救治过的农夫。此刻他们的手里,
不是锄头和烟斗,而是草叉、猎枪、锈迹斑斑的斧头。空气里,怒意在燃烧。
罗伯特第一个站出来,嗓音低哑发抖,脸色涨红:“把他交出来,医生。
”他的儿子还在前线,此时他的脸上写满了仇恨。“我们都知道你在窝棚里藏了个德国佬。
”“吊死他!”“间谍!杀了他!”更多的人跟着喊,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
戴安站在窝棚门口,瘦小的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。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,她没有动。
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脸。
“He is my patient.”(他是我的病人)人群静了一下,
有人低声骂出脏话,更多的声音带着哭腔与愤怒:“他是杀人犯!他杀了我们的孩子!
”戴安深吸了一口气,脊背挺得笔直,
save a life, not to judge it.”(我的职责是拯救生命,
而不是审判生命。)她把双臂张开,拦在门口,声音不大,却足以传到每个人耳朵里。
那些愤怒的脸孔,渐渐变得复杂。有人握紧了草叉,有人低下头踢着泥地。窝棚里,
克劳斯只能听见外面潮水般的喊声,他听不懂英文,但他能看见门口那个瘦弱的身影,
站得那么直。阳光落在她的肩膀上,给她镶了一道光边。那一刻,他明白,
这个陌生国度的女人,是他此刻唯一的守护。罗伯特咬紧牙关,举起了手里的猎枪。
枪口在光里微微闪烁,眼里的愤怒几乎快要爆炸。空气骤然紧张,
围观的村民有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,也有人攥紧了手里的农具。就在这时,
人群后方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。村里的老牧师拄着拐杖,从人群中吃力地挤了进来。
他的头发已经花白,额头和手背满是老年斑。他站到戴安身边,
朝着她身后黑暗的窝棚看了一眼,又低头注视着戴安。“戴安,”他的声音不大,
却盖住了骚动,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?”戴安没有回避他目光,神情坚定:“我知道。
”牧师沉默了片刻,眼底浮起一点疲惫。他想起了上个冬天自己肺炎高烧,
是眼前这个来自东方的女人守了三天三夜,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。他轻轻叹了一口气,
转身对村民们大声说道:“让她先治好他。”他扫了一眼罗伯特涨红的脸和攥紧的手指,
“一个活着的俘虏,对我们的军队来说,比一具尸体更有价值,
他们或许可以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。”他目光最后落在罗伯特身上,
语气坚决:“让他活着,等国王的军队来审判。如果我们当了刽子手,
和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?”人群里出现了动摇的声音,有人开始低声嘀咕,
有人缓缓放下了高举的草叉。罗伯特的手缓缓下移,枪口终于垂了下来。他死死盯着戴安,
声音沙哑:“好。我们不杀他。但你,还有那个德国人,哪儿也不许去。
我们会派人守在这里,直到军队把他带走。”他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恨意。
气氛终于缓和了一点,但那种戒备的空气还没有完全散去。牧师拍了拍戴安的肩膀,
目光柔和:“孩子。愿上帝宽恕你的仁慈。”戴安站直了身体,脸色苍白但没有后退。
她用力点了一下头,然后转身走回窝棚门口,用自己的身体继续挡住了那个伤员。
6窝棚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囚笼。每天,村民轮班守在林子外。他们从不靠近,
只是远远站着,有时候只是背着手、站在树影里,无声无息地盯着窝棚的方向,
仿佛一群狱卒。每顿饭只会放在窝棚外的石头上,一碗稀薄的粥,一块硬邦邦的黑面包,
从不多给一口。送饭的人不说话,连眼神也带着一层结冰般的冷意,放下食物便转身离开。
克劳斯靠在窝棚墙边,透过缝隙观察外面的一切。他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些目光,
有的带着仇恨,有的只是麻木,但无一例外,都在提醒他,他们都希望他死。有时风吹进来,
带着潮湿的青草味,也带来村民低低的窃语。只有戴安还每天来。现在,她无需再遮掩什么。
她会在全村人的注视下,沉静地提着医疗箱,一步步穿过树林,推开窝棚的门,
直视那些不善的目光,没有任何犹豫。她的脚步声,是这个囚笼里唯一悦耳的曲子。
外面世界的敌意越深,他们的交流反而更专注。
那本破旧的英文儿童书成了两人的第一本词典。戴安指着图画,耐心地用英语教他单词,
每一个词都写在本子上,再让他念出来。
“Pain.”“Gratitude.”“Hope.”克劳斯总会用德式口音重复一遍,
发音很生硬,有时候他也忍不住笑出来。戴安偶尔嘴角会抬起一点点,笑意淡得像雨雾,
但克劳斯却记得很清楚——那是她第一次在这里展现温柔。有时,
他会在戴安带来的纸上用木炭画下柏林的街道、老房子的模样,和大学时画的建筑草图。
他画下慕尼黑玛利亚广场的啤酒花园,说他上高中时和同学一起去过。他说,
原本的生活不是战争,也不是飞行。他本应成为一个建筑师,他想念大学课堂里勾画的线条,
只是某个下午,他被抓去当了兵,那段日子,每个人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。他说着说着,
忽然沉默,声音也逐渐变得哽咽,他说他想他的爸爸妈妈,不知道他们在柏林还好吗?说完,
他的泪就这样掉落,砸在他的膝盖上。戴安虽然听不懂全部的德语,
但能读懂他画里的怀念和遗憾。有一天夜晚,星光从窝棚破烂的屋顶洒进来。
克劳斯指着窗外的那束微光,教她念:“Sterne。”她跟着他,一遍遍练习。有一天,
戴安终于向他讲起了南京。她没有激昂的情绪,也没有把痛苦赤裸地抛在光下,
只是把手指轻轻摩挲在膝盖上,平静地说着自己童年时的河岸、灯影,
还有那些至今未能再见的亲人。这一次,她没有再用英语,而是换回了久违的母语。
那些柔软的音节在窝棚里回荡,带着深深的哀伤。克劳斯一句也听不懂,
但却被这陌生的旋律吸引,静静看着她,哪怕只是呼吸也不敢太大声。他第一次明白,
戴安眼里那一层冷静的灰烬,不是与生俱来,而是被战火和离散灼烧过的痕迹。那些沉默,
是从废墟里生长出来的盔甲。她所说的每一句话,哪怕只是关于秦淮河的灯影,
都压得人心口发闷。克劳斯没有试图安慰,也没有多问。他只是很久没有移开自己的目光。
就在那一刻,国籍、语言甚至仇恨的界限,似乎全都失去了意义。